李思维:《归去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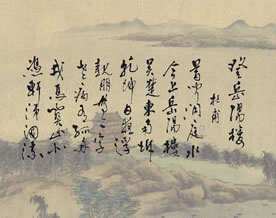
历史上的文化人,或有意冲着它的名气而来,或者被贬南蛮之地,很少有绕过此楼的,也有本来不经过此地的流放者,央求押送的士兵,绕道岳阳楼。士兵们和朝廷犯人本来没有家仇国恨,只要不耽误行程,对于这样温和的请求,往往予以默许。历朝历代想在此处留下一言半句的文化人如过江之鲫。然而真正能经过时间的洗刷,在这片楼墙留下点点墨迹的并不多。能数出来的,就剩下杜甫、韩愈、刘禹锡、白居易、李商隐等几个。他们留下的名篇佳作,使岳阳楼名气上升不少。当然,使它扬名海内的并不是这些人,而是一个普通的地方官和一位朝廷文官的友谊。公元1045年春,风和日丽,滕子京花了很大力气修葺的楼终于竣工,想请一个名人写个楼记,把海内几个大家翻了个遍,发现最合适的就是刚刚下野的范仲淹。正当信函发出去了时候,他又迟疑了。范虽是老友,但现在正处于危困期,自己不好生劝慰,还这样麻烦他?没有想到,楼记以非常快的速度就寄回,甚至超过他们平时来往的信函速度。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只有369字,却阐幽发微,气势磅礴。文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句子很快不胫而走。其境界不仅超越以前数百年的鸿儒,还超越了亚圣孟子的“与民同乐”的思想。如果说孟子和普通百姓之间还有某种扭捏和君子的矜持的话,那么,范仲淹已经把百姓的忧乐当作自己内化的人格追求了。这不是高出好一个层次了么。
其实,范仲淹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日子非常艰难。1046年,他因倡导“庆历新政”被贬,恰逢生命的低谷。这种时候,官场中那些平时整天殷殷笑意的人躲都来不及,滕子京这样一个很少见面的地方官员,还不识时务,邀请他这样一个刚刚走下权力颠峰的人写一篇楼记。这让范仲淹很是感动,政治的无情和朋友的珍贵在心里绞捏、翻腾。官僚集团的倾轧和老朋友关键时候的挂念,加上政治理想的破灭,于是家国、天下、友情汇集成一股郁结之气,喷薄而出,放肆地倾泻在泛毛的黄裱纸上。老练的他,没有让感情过于奔放,而是在369字处嘎然而止。于是一个中国地理上的文化兴奋点和一位历史上文章绝顶的高手相遇了,两者结合得那样恰到好处别有韵致。环洞庭湖一带也许他曾经去过,但是新修的岳阳楼,远在千里之外,是绝对还没有看过。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挥笔而就一篇千古绝唱。人说真正的好文章大多是“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发愤之所为作也”。由是观之,大抵如此。
但是,在抒发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旷古嗟呼之后,囿于他的时代局限,他也许永远没法明白:变革是件极其奢侈的游戏,不是谁能够轻易玩转的一种东西。历史上成功的变革大多因时而成,远如管仲,近有商鞅。后者虽然被车裂,但是他的一套改革方案改变了一个王朝的命运。中国从来不缺乏能员干吏,后来的能干如王安石,精明如张居正,然都不足以以一己之力,推动历史车轮。陈旧的官僚集团在一个王朝的中后期,道德水平已经滑向最低层。以保守官僚为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势力是那样的坚如磐石,使范仲淹的“庆历新政”的呼声来不及渗透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层面,就淹没在守旧者的反对声挟卷起的唾沫中。英雄的成长,大多因时顺势而成。对此,本世纪有个伟大人物深解其味。当一个太平洋彼岸超级大国的总统恭维他“你只用了几本小册子就改变了中国”时,他大手一挥说:我只不过改变了北京附近的一些地方而已。遍翻人类历史,或者横切中国整个20世纪,谁能像他一样翻天覆地地改变一个国家,但是他对个人力量的局限性有着无比清醒的洞察。一个国家,一个文明的集合体,在其后期,随着制度成本的扩张,不可避免地会滑向低效和腐败。不要说臣子,就是皇帝有时面对腐败的官僚集团也无能为力。从正德到万历,嘉庆到光绪,都是以九五之尊,未能扭转一个王朝的败落。上层官僚的糜烂加上皇帝身边亲人的贪婪编织成一个无所不在的囚网,成为改革者无法逾越的天花板。多少忠臣,多少志士,一腔热血都付诸东流。治平的政治理想无法实现,不如归去。躲到一个地方,伴着梅妻鹤子,和着山高水长一同老去。
是磁场总得有个磁极。岳阳楼地处环洞庭湖这一文化磁场的中心,可以算作它的文化磁极。我离开的时候,发现步履艰难,有某种向心力牵引着我。搭上火车回头一瞥,在洞庭湖边看见一个白发老者在垂钓。一股肃然之气,涌上心头,心理嘀咕:千万不要小瞧他。说不准是位归去来兮的老者。
李思维:湖南大学金融学院2003级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