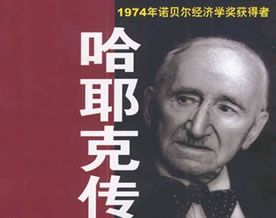成庆:长江漂流与两个时代的理想主义

同样一个长江漂流,跨越20年之后,如今逐渐演变成一种专业性的户外探险运动,越来越强调设备的专业性与探险过程的安全性,长江漂流的含义也越来越逼仄,因为它无法与一个更高的价值勾联起来,也使得漂流只是一项个人的事业选择而已。这一个转变也使得20年后再看当年的长江漂流,难免会对其唏嘘短叹,会因为其不惜生命而感觉惋惜,甚者竟会将之与今天的狭隘民族主义建立起历史的隐秘线索,从而抹杀当年那一代长漂人的精神价值,最终将自己置于后知后觉的制高点上品评前人。从某个意义上来看,这20余年的变化,造成的是一个精神世界不断往后退缩的局面,我们不仅越来越相信,个人主义的意义就是在于个人利益优先,生命的主要价值就在于苟全性命,而且还会开始嘲讽前人在长江漂流中的“堂吉珂德式”的理想主义,或者因为今天历史情境的转移,中华民族这样的宏大历史符号已经被批评成狭隘民族主义,从而也一律否定了当年长漂人为了他们心目中的“民族命运”而漂流的历史意义,这不仅并不公允,也显现出今天人们眼光上的某些盲点。
不过有趣的是,就在最近,一名湖北普通工人依靠一只橡皮轮胎、一个脸盆、两支竹片制成的桨,从重庆漂流到上海。漂流途中,自然艰辛重重,公众也将这一行为视为哗众取宠之举。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名男子的漂流装备上,写有“迎奥运长江第一漂,弥补奥运个人第一漂”的字样。这样一种话语,暗示了这位漂流人的一些心理动机。“奥运”符号激发起来的同样是“民族/国家”的想象,尽管他从事的是非常典型的个人漂流,但是他却颇为相似地与八十年代的漂流人一样,将这样一种漂流与更高的“民族/国家”符号联系起来,获得更丰富的行动意义。
这种意义赋予的方式,与尧茂书显然十分相似,而与今天长江漂流的专业人士存在着相当的差异。漂流专业人员会认为,这是一项专业探险的活动,意义更多在于个人摸索自我的运动极限,而并没有和更为宏大的目标有多少关系,而那位湖北的普通工人,却继续沿袭着八十年代的行为逻辑,将个人的探险与“民族/国家”话语联系起来,在今天的语境下显现出时代错置的荒谬感。
八十年代长江漂流人的理想主义,是将个人与民族存亡的历史目标联系在一起,因此生命并不足惜,因为有更宏大的历史价值在后面支撑。而今天这个时代,长江漂流已经演变成一项意义单薄的体育探险,这并不是要否定这种观念,而是要指出,历史的情境已经改变,我们对八十年代的激情甚至狂热,就算难以认同,也应给予同情性的理解,因为他们恰好在那样一种历史氛围下生活,也碰巧看到了这个国家转型期的某些希望,难免会投身进去,为了一个宏大的目标而奋斗。这20余年的时势转移,造就了另外一种“国家/民族”话语,也使得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在今天难免有同为刍狗之意。如果说,今天这个社会尚存在一种理想主义的话,那也是高度个人化的,与某种宏大话语相区分开的一种精神,但是我一直在怀疑,今天这种理想主义的精神资源总有匮乏的嫌弃,我并不是要求今天将长江漂流再次纳入到“为了华夏文明”这样的宏大话语体系中,而是认为八十年代长漂人的理想主义,就算他们寄托的对象在今天发生了种种扭曲变形,但是其意义也不容否定,反而可以拿来救济今天所谓“理想主义”的某些阙失之处。
成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生,主攻现代中国政治思想史,曾任世纪中国网站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