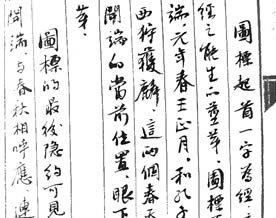陈赟:《天下或天地之间:中国思想的古典视域》序言
“在东方,诞生、滋润和抚养是唯一的事情。”这是诗人海子在其《但是水、水》中的诗句,它默默地“契入寂静而内含的东方精神”。作为诗人的海子把诗理解为对实体的接触,他试图“以诗的方式”,“走向我们民族的心灵深处,揭开黄色的皮肤,看一看古老的沉积着流水和暗红色血块的心脏,看一看河流的含沙量和冲击力,”“希望能找到对土地和河流——这些巨大物质实体的触摸方式。”海子所表述的其实是一个悠久的文化梦想,也是一个指引着那个被命名为“中国人”的族群的梦想。而今我们试图以思想的方式抵达这一梦想,抵达那种特有的对巨大物质实体的触摸方式,以及在此触摸方式中开显的作为这个地方(中国)特有区域的天空与大地,还有在这个区域中展开的文化生命。
一个民族的文化生命往往体现在其经典中,因而,我们选择的途径是对汉语经典作出深度的诠释。在众多的经典中,我们首先选择了《中庸》,这是因为,《中庸》直接指向了中国思想触摸实体的独特方式,因而它历来被理解为(文化)中国之灵魂的直接展现与直接诠释。弗朗索瓦?于连(Fran?ois Jullien)曾说:“《中庸》用很少的篇幅就让读者进入中国思想的核心,因为这篇古代的短论被当作文人传统的基础经典。同时,《中庸》让我们达到一种思想的核心,这种思想随着人们对它的理解吸收,显示为能够成为最普遍的,最易于赞同的:因为《中庸》反映的是没有任何教义的对象,脱离了任何特定理论工具。《中庸》并不思考一个特殊的对象,而是思想‘中’,即通过对世界和我们自己的不断适应得到的平衡,即‘调节’。”“因为这既不是一部旨在揭示‘神秘’的启示录,也不是力图要证明一个真理的思辨论著。”“这部著作什么都不揭示,也不建树任何东西——只是阐述。如果说它导致对道德基础的思考,那是因为它没有求助神学,也没有求助本体建构。这样,《中庸》就回答了处于人类反思基础上的这样两个问题,而我们习惯上把这两个问题分别对待:实在从何而来?理想状态何在?在此,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因为‘真’固有的能力从根本上讲是与‘善’合而为一的。”与其说《中庸》以一种令人惊讶的方式抵达了中国思想的核心,勿宁说,在中庸中,中国思想确立了自身。
这里所谓的“深度诠释”,指的就是于连所说的那种既不求助于神学,也不求助于本体建构的经典书写方式。在我们看来,作为一个事件的诠释活动,发生在通过过去与未来打开现在,同时也根据现在而打开过去与未来的双向往来的过程中。因而,诠释的深度不仅仅取决于它通达生命之当下境遇的深度,同时也在于它容纳历史、沟通未来的深度。深度的诠释既是思想与文化上的“报本返始”的活动,同时也是一种当下发生的重新开端。因而,以深度诠释的方式打开《中庸》,不同于文字学家之训诂,不同于从《中庸》文本到《中庸》本文的技术性分析,也不同于那种回到原意、本意的客观主义幻象支配下的经典书写,同样,也有别于那种以思辨的方式抵达的形而上学的、本体论的理论构造活动——在今日,这些已经成为理解经典的主导方式。当然,这里并不是要对文字训诂、思辨的本体构造等进行先在的否定,否认其存在的合法性,而是期待开启别样思考的可能性,从而增加理解中庸的维度,这种别样思考的可能性本身就是思想的可能性,但正如海德格尔所说,思想需要时间,它的时间和它的时间。……
深度的诠释,作为一种思想的事业,要求我们不仅面对作为文本的《中庸》,也要面对由“中庸”所历史地开启的巨大而真实、然而又从我们的视线中不断后撤的历史文化世界。因而,我们试图在整个古代中国思想的视野中理解《中庸》,同时也通过《中庸》理解那个与“中国”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古老而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思想的本性是相互通达的,不同的文本不能被作为既定的不可逾越的封畛,所谓的以《庄》解《庄》、以《易》解《易》、以《庸》解《庸》等等,毕竟是在思想的事情中人为地圈定封畛。这样,我们就只能加剧《庄子》所慨叹的“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的状况,而愈来愈远离“道通为一”(《庄子?齐物论》)、“一以贯之”(孔子)、“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周易?系辞》)的理想。在今日,作为知识存在方式的“科学”加剧了这一状况。“科学领域分崩离析。处理各自对象的方式迥然不同。各种律令在分崩瓦解中纷然杂陈,如今只靠大学和系这种技术组织把它们拢在一起,并通过给专业设置实践目的的方式实现其意义。”与此相应,“在社会层面甚至在社区层面内设定目标的变革以及对约定俗成进行‘变构’的诸多互异的尝试确实引导了现代的研究。”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将《中庸》交付给哲学、形而上学、本体论,还是人类学、宗教-神学、政治哲学,都不可避免地与这种区域性的目标联系在一起,由此获得的“科学性”阐释与“该”、“遍”、“全”、“备”的“古人”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人们也因此将自己放置在局限在某些特定的不相贯通的方面、层次的“不该不徧”的“一曲之士”的位置上。
《庄子·天下篇》等所表述的上述理想,同时也是思想历史上的实情。在古代中国的经典中,可以看到如下的现象:不同经典的文本之间具有一种“互文”的关系,可以在它们的相互指引与穿越中,更好地抵达一个具体的文本,正如在园林建筑中,其不同的区域可以通过门窗相望;这与希腊哲学中的状况相反,那里存在着的实情不是经典之间的互文见义,而是不同的意见的论辩而打开的竞争性话语。竞争性话语的自觉定位导致了逻辑论辩在哲学陈述中的核心位置以及对不同理论(theory)的消费行为,而经典的互文则历史地形成了以在差异中寻求相互通达、相互指引的境域性目光的要求。在这一目光中,重要的不是去证明某个预先获得的假设,而是去阐明作为被谈论事物背景的境域总体以及在这总体中为事物定位;而这种相互指引的境域总体,并不能仅仅通过求真意志与认知活动给予,还必须考虑到由身体的相互化生作用而导致的“互文”现象,这个意义上的“互文”意味着,在“本文”中发现了自己身体之“文”或在自己身体之“文”中发现了“文本”之“文”。以这样的方式去打开经典,就不仅仅指向心智的层面,而是朝向身体及其活动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深度诠释在某种意义上可谓是一种“身心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