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异:孔子在庄子书写中的变象(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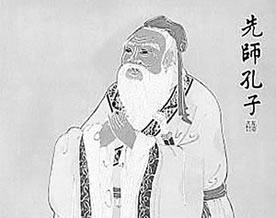
孔子在庄子书写中的变象之一:
穷——孔子自身形象的时间性疑难
庄子的所有写作,可能都源发于那个混沌(浑沌)之喻的故事,那个生命感通的悖论!
这是《庄子·应帝王》中的“卮言”:
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这是一个虚构文本,似乎不会是历史的事实!所谓一个被“改写”了的宇宙创生的神话故事,庄子以其卮言的文体写作所展开的故事,如果考虑到这个故事是所谓的《内篇》最后一篇的结尾文字,以及与《应帝王》这个篇目以及整个文本的内在关联,浑沌(或混沌)故事中的三个虚拟人物似乎对应于神巫季咸、壶子和列子之间的对话和交往——不过这几个人物之间的对话还只是“寓言”式的。

但是浑沌之卮言却暗示着,因感通而死亡,但又是新生的时机;同时,也是好客或好意的后果——因此,任何的给予可能都是危险的,任何的沟通可能是不可能的?在此两难的背景下,当下的我们如何解读庄子?庄子其实在回应中国文化传统本身的那个“绝地天通”的开端的危难,对开端的回应,似乎更加彻底,因为他面对了感通本身的两难!如果感通导致生命的死亡,那么如何面对这个打断?是否不得不对孔子已经形成的感通的范例有所变异?
这里,在混沌开窍的描绘中,还有着“倏-忽”声音节奏的回想,有着名字的问题,而且渗透了暗讽的气氛。也许这也是对传统的伏羲和女娲关系的解神话。这是庄子变异书写的范例!
如果历史的生命之间有着内在的回应,庄子对孔子的书写一定有着历史命运的关联。但是,我们不得不深入事件性的思考之中,尤其是孔子如何看待自身的,或者孔子在庄子那里的生命形象如何表现的?
